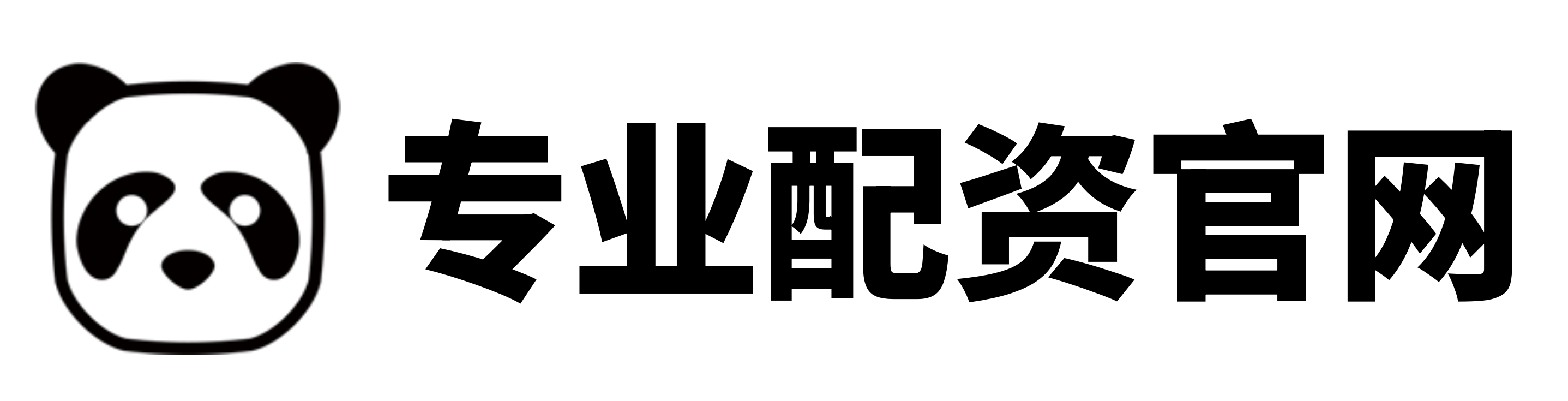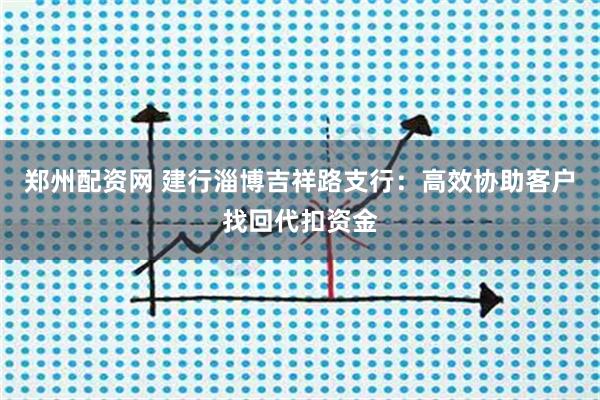配资平台开户 七国诸侯并起,吴楚兵临关中,汉景帝平乱削藩
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配资平台开户
公元前154年,汉朝中枢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撕裂。七位诸侯王联兵反汉,战火蔓延半个中国,中央政府危在旦夕。
吴楚为首,赵国紧随,列国应声而起。宫廷震动,京师不宁,汉景帝不得不做出一连串激烈而决绝的决定。
削藩之命,封疆之怒汉景帝三年,削藩风起。
景帝刘启即位不过三年,宫廷安稳,边疆无战,表面风平浪静。朝中却早已有人按捺不住,主张清理积弊,整顿诸侯。诸侯封国盘踞地方,权力几与皇权分庭抗礼,成为汉初最大隐患。
展开剩余89%高祖开国时封同姓子弟为王,意图稳固宗室,建立“汉室一体”的宗族政治体系。可几十年过去,这些王国逐渐演化为独立政权。吴楚赵三国,尤其肆意。设官授职,私筑宫室,擅铸铜钱,割据一方,自成体系。
吴王刘濞,乃高祖兄子,自封为王六十年之久,年资最长,兵甲最盛,诸侯中首屈一指。他多次请求入朝见天子,却被拒绝。因其子曾与太子争执,被废除世袭资格,从此怀怨在心。兵权不减,权心愈增,吴地愈发难控。
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,与吴王声气相通,皆久居一地,自建府兵,与地方官吏对抗,漠视诏令,拒不受检。朝廷派遣使者至王国,不得接见,奏章被扣,税收不交。关东王国已不再是中央一部分,而是独立于汉廷的政治力量。
削藩意见由御史大夫晁错提出。他通晓律令,精于政术,主张将诸侯权力收归中央。他认为“削藩不急,则祸难遏”,力陈诸侯之危,建议景帝乘盛世强力推行。
景帝采纳。下令自吴、楚、赵开始,削除多余郡县、兼并封地,回归中央统治。郡守太守改由朝廷任命,禁止王国设置属官。原本封地十郡者留三,十五者留五,撤除余者。
政令刚下,震动诸国。王国尚未明言反对,但实际操作层层阻挠。吴楚两国接连拒绝交地,遣散兵士名为“休养”,实为就地屯兵。朝中紧跟第二诏,申明削地之命为法令,不得违抗。
诸侯不答。赵国不动声色,暗中招募乡勇。吴王公开取消部分府职,私下囤积粮草。楚王将亲兵悄然集结于郊外训练。百姓未明其意,但风声早已走漏,市井传言已变成恐慌。长安朝中诏令未止,地方已在沉默中备战。
半年之间,关东七国开始互通消息。吴王最早主张联兵,他调使往赵楚,信使带往胶东、菑川、济南、济北。多为同族,亦为亲戚,封王之初皆拜于高祖麾下,今皆立国已久,兵民万计,财赋丰厚。
吴国接信最早,赵国回信最快。楚王一度犹豫,终因子弟任职被裁而怒。各王皆称“受削之辱”,共议对策。议定后,七王达成共识:若削地不止,便同举兵。
中央尚未察觉决意已成。景帝遣中使巡行七国,求其自请归地,各国皆称病不见。其后两月,吴王府军扩至三万,城中兵备充足,粮库日夜进粮,商道半闭。诸侯反心已不可遏制。
七国连动,兵锋逼近长安起事没有前奏。
正月初,吴王率军出江都,分三路攻梁。梁国为景帝之弟刘武所封,忠于中央,为关东屏障。吴军突然南进,破下邳、郯城,转而北攻济阴。梁守军抵抗不足三日,弃城南走。
同月,楚王刘戊发兵彭城。楚军渡淮,兵分两路,西取寿春,北向山阳,连破数郡。赵王刘遂于代地举兵,兵向常山,直逼魏地。胶东、菑川、济北诸国应声而起,各自调兵,不发战书。
七国总兵力约数十万,实际可战之兵估近二十万。吴楚两国联军为主力,楚兵纪律尚严,吴军以轻骑冲杀著称。赵兵多为步卒,武器简陋,但军号整齐,声势不小。
起兵口号为“诛晁错,清君侧”。明为靖奸,实为逼宫。诏书中避称天子为敌,斥晁错为专权小人,以朝政偏移为借口。七国战旗下皆立“匡扶社稷”之旗,民间多信其词,沿途未遇实质阻力。
梁国形势最为危急。刘武死守睢阳,请兵于长安。朝中震惊。景帝一夜召集群臣,军令未定,捷报已失三郡。晁错请速遣兵,周亚夫请缓调动,以避锋芒。张释之请宥诸侯,暂缓削地。
景帝决定不撤诏。第二道命令令周亚夫总兵,东征七国。前令未发,吴军已逼近濮阳。赵军斜插河间,逼近成皋。形势逼人。吴楚合兵西进,目标直指关中门户。
吴军连破梁、济,楚兵攻陷阳夏,赵军占据魏郡。景帝急召诸将,未及调动,吴王已派先遣部队沿济水西上,兵锋接近函谷关。
长安城中,人心惶惶。驿站日夜不息,诏令连发三道,兵符九转。百官面色沉重,市中传言盛起。三月之内,王室安危几至悬于一线。
至此,吴楚赵三国形成东西南北之合围态势,七国兵力虽未汇合,但在战线上已构成合围之势。中原震荡,朝廷仓促。削藩之局,转瞬成战国重演。
晁错伏诛,周亚夫挂帅七国兵锋压境,关中戒严,汉景帝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局。朝堂之上,群臣议论纷纷,却没有一人能给出破局之策。晁错作为削藩政策的设计者,成了众矢之的。
他没有退让,坚称诛乱臣贼、平叛到底。可战局节节败退,地方连陷数郡。朝臣越来越多地将矛头对准他,不为功过,只为止乱。长安城外已现乱军游踪,诸侯所拥兵力远超预期。朝廷欲救大局,必须先断一臂。
景帝终于决断。公元前154年三月初,晁错被赐死于长安街头,未及辩白。尸首弃市,不设棺椁,官民围观,喧哗不止。朝廷刻意将其罪名定为“惑政擅权,激乱诸侯”,用以回应七国的“清君侧”之言。
但叛军并未止步。吴楚之兵未见后撤,赵国依旧沿太行布阵,齐地各国调兵更频。原本的借口已无,真正的意图暴露。诛错止乱,不过是虚名。
汉景帝不再犹豫,立即任命太尉周亚夫统兵讨伐。周亚夫为文帝旧臣,熟稔兵法,治军严整。接兵符之日,不见欢言。未入都门,便开始调阅各地兵籍。
周亚夫调兵路线明确。梁王刘武守阳夏,战力有限,兵源匮乏。他选择绕过东线战场,从河南郡起兵,北连魏地,南截楚军,主打围困断粮之策。他不设锋锐之势,而以防守为主,静待七国军力自行崩溃。
进兵之初,他命军不得出营一步。粮草随军,三日一检。令行禁止,连主将亦需通报方可出营。与诸侯之军气氛浮动、号令混乱形成鲜明对比。
楚军自认为兵强,将欲速战,主动攻周军外围营地。周亚夫不应战,仅以弓弩设伏,弃地而走,引敌深入再设关隘封断。楚军三战皆无功,粮路不继,士气渐降。
吴军则在濮阳受挫。梁王死守睢阳,未被攻破。周军援兵断绝吴军西进之路。吴王刘濞不得不改变计划,命部下退回江都。途中不断遭遇汉军截击,数万之众逐步瓦解。
赵王刘遂所部本欲北扰燕地以牵制朝廷,然被代王和中山兵所阻,一路苦战,终因兵力不足,主动回撤。赵军退回邯郸途中,被旧将叛变,宫门失守,刘遂被擒。
三个月内,周亚夫未打一场正面决战,却逼得七国之军无一立足。楚王刘戊在部下劝说无望后,自刎于军帐。吴王刘濞逃往东南闽越,途中病重,服毒自尽。余部投降者众,部分郡县未战而降。
景帝接报时,七国仅余残兵散将。命令赦免无罪百姓,分兵收复各地。整个叛乱,从爆发到覆灭,未及百日。
爵位不废,权力尽夺七国平定后,中央收回全部反叛王国之地。吴、楚、赵三国被废,土地分设为郡,重新派遣太守。其余响应诸侯,被诛王废爵或削地除权。七国尽失昔日威望。
但景帝并未全面废除王国制度。考虑宗室稳定与权力平衡,他保留王号,只剥夺其实权。封地虽在,已无治政之权。郡县收归中央,王府仅可祭祀祖先,不得设官理民。
诸侯不得设兵。原有私军一律遣散,城池收归朝廷。各地军器造坊关闭,兵甲归仓,军吏改编。王国不得收税,不得设法,不得审案,连地方建设也需朝廷批准。
景帝以此为界,确立郡县制为国家根本架构。诸侯之王仅存名义,不复权势。关东之地,从此由京师直辖。
朝中设刺史监察地方王国,巡视郡县,直接向皇帝汇报。诸侯王无权阻拦,也无权更换属地官员。宗室子弟不得自立为王,袭封必须经天子诏命。
一些未参与叛乱的王国主动上表请献地,以示忠诚。长沙、淮南、齐地诸王皆自请削地,避祸于未然。中央得以顺势推行制度变革,未动刀兵而扩权至全国。
这场战争之后,王国制度被彻底改写。封王仍在,但王国已成空壳。宗室贵戚仅为荣耀,不再执政。景帝借由七国之乱,完成一次彻底的中央权力重构。
朝廷从此不再畏惧诸侯合谋。后世虽仍有王位更替,但再未出现多国联兵叛汉之事。七国的兵火,烧尽的不仅是一场叛乱配资平台开户,更是西汉初期分权体制的最后残影。
发布于:山东省捷希缘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